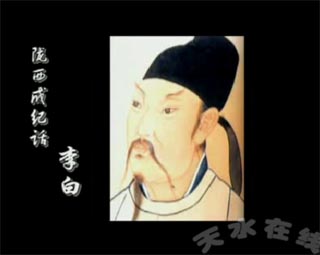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�ص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Ÿ�Ԋ��r,�O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ɂ��ɻ��y��Ć��},һ�ǹ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Ÿ����x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L(f��ng)�D(zhu��n)׃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뾳�����A֮��,����֪���ںηNԭ���N��Ԋ�x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Ԋһ��δ�x,���硶é�ݞ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Ƹ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Ʒÿ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Ÿ�Ԋ�x���T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ƽ��Ȫ�۵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ݳ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Ԋ��δ�롶�����sԊ����ʮ��֮��(n��i)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֮�����ʮ�ĵ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Ԋ�x���ʮ��֮��(n��i),���ɴ�ȥ���x�Ÿ�һ�ҵ���ۙ,�ɴ��γɱ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һ�ǵľ��档ǰ�ߴ���c�x���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Ƨ����ƫҊ,��?q��)��]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첻�o�P(gu��n)ϵ,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
�����҂�֪��,�Ÿ�һ����Ԋ��ǧ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һǧ�İٶ���,�Ÿ�Ԋ�ռ���Ҫ�Ա��ε��S�Q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ľ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ȶ���]��֮��,�ʌ��Ÿ�Ԋ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y��,���x���ߌ�ԭ�o�}Ԋ�Լ��}Ŀ��rҊ,�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���}Ŀ��(y��ng)��Ÿ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Ԋ��һ���ǶŸ��H��,����©���e�`���댍���y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LjD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ĸ߶�����֮��,��ʹ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Щ�f������ԏ��Ԋ�����r��,ҲҪ�������C,�a������,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v���ɡ���_,�e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bָ��䏈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ۻ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ȥ̽���Ÿ����]�ҵ���ۙ,ֻ��Խ̽ԽÓ�x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��ʮ��֮һ,���@����Ԋ��һ�ҏĹ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v���³��ŏ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Ѯ��Խ�]��,ʼ������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o���x,ֻ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غ�ĵ�һ��Ԋ,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Ÿ����е�ԭ��,���Ԍ��˵Ġ��h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Ÿ��ķ�ˮ�A�^�]�ൽ�_(d��)�Ҵ����R¹��,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Ҵ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ˮ�³�,�^�ݴ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Ÿ��e�ҏIJݴ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ҹ���ܶ�μ��,��סһ�ޡ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ڞ�Ԋ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`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:�����R��Ȫ����μ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,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ɽ���йų��zַ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ڶŸ����á�ԊҲ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˷��˶Ÿ�һ�Ү�(d��ng)���߹ٵ���(j��ng)�ذ����ݳ�֮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ߌ�����һ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Ԋ֮��,�˂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ɶŸ�ȥ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,���Զ�Ԋ����߀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@һ�f���І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կ�����Һ�ʮ��·��,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ʮ���A��,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?�ƴ��Ľ����(zh��n),ꃴ���̖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\؛���Ƽ����,���Ƿ��A,���Һ��b��Ҋ���(zh��n)�Ź����ɘ�,���Ҳ̎�ӹ�,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кܴ�ą^(q��)�e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ֶ�Ҳ��ܾ���,�Ÿ�ֻ�ܰ������ݳǃ�(n��i)��ǽ�,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,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Ÿ����ҿտ��ߝ�,����һ�X�����r,�R���_���ͬ�Ȏ������,һ���˱�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ȵ�·;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Ԋ��,�Ÿ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,��Փ���f��ס���Ϲ���,�@�Ǵ��І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ʢ,ɮ�˱���,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猢Ҫ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ҵ�ʲ��Ħ��ҲҪ��(j��ng)�^һ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һ����ס�Ϲ���,�]����},���e��ס��,�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֮���к�ɽ,�籾����ʯ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ɽȫ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,�����ˌ��ˌ�����Ҳ�Б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,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,��Ҳ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֮̎����DZ���Ԋ����֮��,Ҳ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Ϲ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һ��֮��(n��i),���Ϲ���Ԋ�t��ʮ���ų��F(xi��n),Ҳ������ɽ֮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֮�����݈D�I(l��ng)ͬ�Ⱦ䡱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ط�־�d,��ǬԪ�g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ߞ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ɼ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֓�(j��)��̫ƽ�h(hu��n)��ӛ����֪,����ǬԪԪ��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�ij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h,���ν����ǵĽ����Ϳh,��ʷ�d�w����ݠ��ͬ��,����ɿ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˞霐�aԊ��,�����ԕr���ݶ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܊�¶���,�մ˶�Ԋ��(y��ng)�顰���D�I(l��ng)ͬ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Ԋ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ڽ����Ϳh��,���һ����صǼ�ļ��ӵ�,�����Ͻ�̔��ǧ����ȫԊ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Ϳh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Rǰ�_�e���γɵij��ɽ,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,���R����,߀��ɽ�ַQ����֮ɽ�����۵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о͌����ăx�Ѿ�,�С����~̫���_,���R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ٝ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֮��ʮ,�С��ؕ���Ѩ,�xӛ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֮ʮ�ĸ���һ���T����ص�Ԋ,�z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��(n��i),�ʺ��˳��J(r��n)�Ÿ��Ľ����Ϳh�Ǻ���ˮ߅��(j��ng)�^,���]�Ќ������Ǻͳ��ɽ��Ԋ,�ɞ�N�N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`,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r�Į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Ÿ�һ�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��Ϳh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ˮ�е��m��ʯɽ�A��,���^ƽ̹,�^ʯ�{,��̽ʯ��,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,�mƫ�h(yu��n),����һ�ӵ��|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ؾ��ڮ�(d��ng)?sh��)��^���c��,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ǧ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,�M�в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㶬ѩ��(y��n)��,ɽ���U��,�����܌������چ��ĶŸ�,�h(yu��n)̎�^�����,סɽ�¼�(x��)��ɽ��֮��,�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挍�ij��Ԋ����L�Ì��Ÿ��Ƿ���^��صĠ�Փ,Դ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sԊ��֮ʮ�IJ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r��һ�N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猢��Ԋ���ڷ��R��֮Ԋ֮��,߀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?
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ý��˂���Փ�Ÿ�ȥ�^�ɮ�(d��ng)�h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x�Ÿ�Ԋ��,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uע��Ԋ���ڶŸ����ݺ��]�ϵ���ۙ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һЩʧ�`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В��u����֮��,��ҹ�ͬ��ӑ,���о��Ÿ��]��Ԋ���ؕ�I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|

 ��ӡ���
��ӡ���